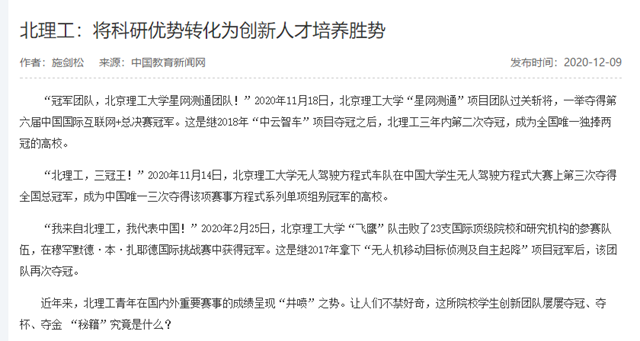[中國青年報]平凡英雄與首都學子面對面
發布日期:2006-01-17 閱讀次數:
《中國青年報》2006年01月13日
本報記者 潘婷 史照棟 通訊員 溫常青 戴慶明 楊好雨整理
http://zqb.cyol.com/gb/zqb/2006-01/13/content_119957.htm
這些天來,獨臂英雄丁曉兵的名字回響在大江南北。這個20年前在戰場上失去右臂的硬漢子,在走下英雄的“圣壇”后,20年的時間里,在每一個平凡的崗位上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與職責。1月10日,這位平凡英雄走進北京大學,和來自北京各高校的同學進行真誠的溝通與面對面的交流。
丁曉兵:回顧這20多年,感觸頗多。如果要給這20年集中起來用兩個字概括的話,我想來想去就是“考驗”。我覺得這20年對我個人來說,我在享受崇高榮譽的同時,也在經受著考驗。
我是一個兩世為人的人,我死過一回,我非常熱愛自己的生命,所以當時我從戰場上昏迷兩天三夜醒過來的時候,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生命寶貴,活著真好。接下來的問題是:不是活著就好,而是想這輩子怎么活,既然我珍惜自己的生命,那么這個生命怎么樣可以活得有質量、有意義,附加值高一點,是我一直在思考和實踐的問題。
北京理工大學學生耿卓研: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像今天這樣的和英雄距離這么近。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想什么是英雄?我覺得您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學習的地方,你就是軍人中的海明威。
我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支撐著你一路走過來,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你的人生追求是什么?是什么促使你作出了今天的選擇?
丁曉兵:我覺得最根本的就是對生命的熱愛。一個人生命的長短我們可能無法把握,一次戰爭、一次意外都可能會出現我們意想不到的結局。但是有一條我們是可以做到的,就是通過我們的主觀努力,找到合適的載體,拓寬生命的空間,拓展我們生命的厚度。在這種拓展當中,能使我們的生命得到充實。我們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不白活一輩子”。這一輩子活得很充實,活得很有意義。我想這恐怕是每一個生活在現實生活中的人都會追求的。
只要我們把自己融入到社會,融入到人民的利益,融入到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極大的拓展,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
清華大學國防生趙曉琳:我早就看過您的事跡,我對您非常崇拜。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里面的主人公也是一個特別有人格魅力的軍人。我希望我今后可以成為一個像您一樣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利益可以犧牲自己一切的人。
本科畢業的時候,我有很多的同學都進了外企工作,他們的收入比我們軍人高很多。但是,今天聽了您的事跡后,我覺得做一個軍人很有意義。剛才您說把自己的生命和國家的利益緊密融合起來,我覺得您是真正做到了。我想問您兩個問題,您心目中的英雄是誰?另一個問題就是您覺得作為一個軍人,對社會應該有怎樣的責任?
丁曉兵:我覺得我身邊就有很多的英雄。20多年前我參戰的時候,我的副班長肚子打裂了,當時腸子就出來了,但是戰斗非常激烈。最后,他把自己的腸子往肚子里一塞,到犧牲以后還睜著一只眼,閉著一只眼做著舉槍射擊的姿勢。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還有他的母親,后來到部隊來找兒子,兒子不在了,老人家哭得死去活來,但是當最后部隊領導問老人您有什么要求的時候,老人只問了一句,我的兒子為國家立功了沒有?當知道自己的兒子立了一等功,老人就哭起來了。當時老人為了不影響部隊的工作,連夜就回家了。這個老母親不是英雄嗎?當然我還受很多傳統文化的影響,過去我很崇拜岳飛,我很小的時候就聽過評書《岳飛傳》,我也知道文天祥,還有毛澤東、鄧小平。他們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說到責任,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責任,對家庭、對社會、對人民、對祖國也對自己。作為一名警官,我們擔負的使命是保衛國家安全,為人民創造一個安定、和平的社會環境。當然,我對我所在部隊的官兵也有一份責任,就是帶好部隊的責任。對我的家庭,我作為一個男人也有責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蔣崇文:自從媒體報道了您的先進事跡以后,我對您有了一些了解。我一直關心的一個話題就是20年前您是一個戰斗英雄,而這20年來您也一直在學習。您在日記里寫道,別人用兩只手可以做到的,我用一只手也可以做到。那么我想問,是什么讓您有這種不斷學習的動力?讓您在變換新工作崗位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己?
丁曉兵:其實有很多我是做不到的,比如說鼓掌。
在戰場上我曾經想到過自己可能會成為烈士,但是我真的沒有想到會傷得那么重,而且失去的是寶貴的右手。所以,當我從醫院醒過來的時候,我拼命地對醫生喊讓他把我的手縫上去。當時醫生也在哭,我一看就知道我的手接不回來了。但是人總是要面對現實。后來我就留在部隊了,在工作和學習過程當中也確實遇到很多困難。但是20年下來以后,我有這樣一種感覺,有的時候身體上的缺憾,如果把握得好,反而會成為激發我們上進的動力。
走下陣地之后的20年,可以說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變化非常大的20年。我總有一種被社會和部隊建設的大潮所淹沒、所淘汰的危機感。和平常的人相比,我的文化底子不厚實,而且我失去了右手,這確實是一個劣勢。如何正視這個問題,如何彌補這個缺陷,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我覺得只能用知識、用先進的思想文化來彌補自己身體上的缺憾。在和部隊的官兵交流當中,大家都說學習是一種苦差事,但是我覺得學習是一種享受。在汲取知識的同時,我人生的缺憾可以得到一種彌補。
還有一個動力就是因為我長期在部隊基層工作,這種工作實踐逼著我去思考、去學習,你不學習就會落伍,你不學習你就失去了領導權和發言權,在部隊說話就沒有分量。
北京大學學生丁杰:我本身也是一個學生共產黨員,在當前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您的事跡深深地感動了我們,您應該成為我們當代青年學習的榜樣。您剛才總結的“考驗”兩個字,讓我感觸很深。
瞬間的壯舉也許很容易造就一個英雄,但是只有在漫長的人生中,才能真正考驗出一個英雄。20年前您作為一個光榮的戰士,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利益,在血與火的考驗當中,您是一個英雄。20年后您面對鮮花與榮譽,您以非常的氣概走過一段奮斗之路,我想您的英雄稱號是更加熠熠生輝。
我們當代大學生將要面對很多挫折,也會面臨很多人生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選擇,面對個人利益、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選擇,我想您的事跡給我們指引了一個前進的方向。我希望我能代表北大學生表一個決心,我希望在以后的學習和生活當中來全面向您學習,學習您的勇氣和力量,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做當代的新青年。
最后我想提一點小小的要求,我希望您對我們當代大學生,或者是當代的青年談一點期望,給我們指點一下方向。
丁曉兵:我在自己家里書寫了兩句話叫“俯仰無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我用來自勉自己作一個無愧天地的人。我理解的天地就是我們的黨,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群眾。我在努力地做這樣的人,我也希望我身邊的戰友、朋友、同志都能夠做這樣的人。
首都師范大學學生劉娟:您一開始讓我感動的是在戰場上的果敢。但是我看了您的事跡以后我越來越被生活中的您感染。
我有兩個問題,剛才您一直在說您這么多年生活的動力就是對生命的熱愛,那么我想知道這20年來您最開心的是什么?第二個問題就是,在20年前,您負傷后本來是可以選擇去更優越的地方工作,但是您卻選擇了基層,那么是什么樣的人生軌跡讓您選擇了去基層?請您告訴我基層的生活經歷對您這20年的經歷有什么樣的影響?
丁曉兵:我覺得最快樂的事就是認識到自我,并能戰勝和超越自我;就是到基層這20年下來我覺得自己還行。
一開始到連隊去的時候,我自己在犯嘀咕。其實,戰勝傷殘,戰勝生活中的各種艱難其實并沒有那么難。我現在回過頭來想想10年前的各種生活、矛盾,現在一看只不過是一個小坎兒而已。
北大學生陳昱良:您在中國的軍隊干了20多年,那么中國軍隊的戰斗力究竟怎么樣?根據中國軍隊目前的戰斗力,怎樣應對未來的信息戰和電子戰?
丁曉兵:作為一個軍人,我對我國軍隊的戰斗力是信心十足的。對于信息戰,現在軍隊也在加強我們的信息化建設,而且力度很大,步伐也很大。有機會歡迎你去我們的部隊現場感受一下部隊的戰斗力。你去問我們的戰士,問每一位中國軍人,他們都會給你一個堅定的回答,我們一定能夠擔負起這個歷史使命。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王淼:我想問您兩個問題,聽您的事跡我想起了幾十年前的雷鋒,他和您一樣有很多的事跡。在雷鋒同志生前的一段時間,到全國各地作報告占用了他很多的時間,他在一定程度上被盛名所累了。那么您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與雷鋒相比,您覺得自己的定位是怎樣的?是希望踏踏實實地繼續做下去,還是希望作為一個時代的典型,用自己做過的事情或者是正在做的事來感動中國的學生?
第二個問題就是雷鋒之所以在生前的后半部分在某種程度上被盛名所累,是因為那時候是一個塑造英雄的時代,您覺得現在還是一個塑造英雄的時代嗎?如果是的話您如何比較自己和雷鋒的相同或者是不同,如果不是,您希望自己是怎么樣的一個人?和雷鋒有什么樣的不同?
丁曉兵:你的問題非常深刻,對我也非常有教育意義。其實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和偉大的雷鋒相比。我就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普通的軍人、黨員,而且是一個失去右臂的軍人。我真的感覺到我做得還很不夠,我的工作當中還有很多的缺陷和缺點。我有閃光的一面,也有平凡的一面,還有不足的一面。
至于說這個時代需要英雄嗎?我覺得還是需要的。我覺得一個沒有一點英雄氣的民族,一個沒有一點對英雄精神崇尚的民族,是不可能有朝氣的。
過去我們和很多西方強敵交過手。我們的武器都比人家弱,但是到最后我們還是戰勝了他們。我看過一篇文章,描寫的是志愿軍戰士。當時美軍在高地上就看著我們的志愿軍戰士像一排排原木一樣,滾滾地向前沖來,倒下一批后面的接著上,最后把美軍看得不敢放槍了,靠的是什么?就是精神,一種報效國家、報效人民的戰斗精神。雖然我們現在是市場經濟,但是對我們國家也好,對個人也好,都是非常需要精神的。一個失去精神支撐的民族、軍隊、個人,我覺得都是很難發展的。
北京師范大學學生高耀華:您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兩個字“感動”。我感動的并不僅僅是您在戰場上的幾個小時,更感動的是您這20年來的堅持。您剛才說您第一次負傷以后醒來第一句話就是“活著真好”,但是在抗洪搶險的時候您又沖在最前面,所以我想聽一下您對生命的認識。
丁曉兵:可能我經歷過生死關頭,所以對生命的意義就認識得更多一些。我九歲的時候也差一點被水淹死了。第二次就是我負傷的那一次。前天我和我的一個老班長聯系上了,我們在電話里都哭了。當時在路上,血一直在滴,中間就休克了,我的班長就掐我的人中,拼命地喊你不能死啊,快到了。我被掐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插在腰帶上的胳膊。最后看到擔架隊我就倒下去了。后來醒過來的時候,我發現自己還活著,那種活過來的感覺很難用語言來形容。
因為那時候還不到19歲。所以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生命對我們個體來說到底意義何在?如何使生命的價值、質量能夠得到提升?應該說20年下來以后我找到了這條途徑。具體的講我是把自己融入了部隊。
我第一次負傷以后,很多單位要求我去工作,應該說當時我面對著很多的機遇,誘惑也很大。因為畢竟少了一只手,在部隊能不能發展,能不能實現我對生命質量的追求呢?我是做了很長時間的思考。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回來以后我老是看見媽媽流淚。我問她怎么了,她不和我說,不過后來我知道了。她擔心的就是不知道我在部隊將來還有什么發展?她甚至擔心這個殘廢的兒子將來能不能找到一個老婆。所以當時地方對我的誘惑是很大的,但是我覺得人要找一個適合自己發展的平臺,我就覺得我自己適合部隊,我覺得這個平臺更適合我發揮自己。
當時我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學習,二是工作,第三條是要到基層去。20年以后才覺得,那時候的選擇現在看來還是很理智的。
北京理工大學學生耿卓研:我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我們在學校也參加過軍訓,部隊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永爭第一。有一句話,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一個好士兵。我知道您曾經說過一句話,您說您愿意做一根翠竹,有骨有節,頂天立地。我想問您的骨和節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支撐著您頂天立地的決心?第二個問題就是您認為這是一個需要英雄和英雄精神的時代嗎?在這樣的時代中,您的事跡具有什么樣的意義?
丁曉兵:你剛才講的不想當將軍的兵不是好兵,我再補充一下,天天都想當將軍的兵肯定也不是好兵。你的第一個問題,實際上我前面已經回答了一部分。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實現個人和集體利益的高度統一。我們現在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我們的價值取向、人生追求,可以說是呈現了日益多元化的趨勢。但是有一條,無論社會怎么樣發展,怎么樣多元,作為一個集體、民族、國家,在這種多元的價值取向當中,必須要有一個主導的東西。不然就像一棵沒有主干的大樹,是長不大的。
現在的官兵思想也有了很多的變化,社會上的一些思想也在影響著我們部隊的官兵。有人問我,丁曉兵你現在還在講犧牲奉獻嗎?我就問他,如果我們的民族、國家、軍隊不講犧牲奉獻,不講社會責任,這個軍隊、集體、國家還有希望嗎?
當然我們不能把兩者割裂起來,對正當的,合法的個人利益我們還是要保護的。
清華大學學生劉煒華:我們的同學來的時候告訴我非常希望有機會見見您,您能不能在合適的時間到我們清華大學為我們的同學們作一次報告。
丁曉兵:可能在三月中下旬吧。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王淼:我覺得,作為大學生需要我們從您的事跡里學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選擇自己的職業。您的事跡給我的啟發就是在找工作的時候要自我解脫、重新定位。我想知道,那么您是如何卸下英雄的光環的?在您選擇了到基層去的時候您有什么樣的心理負擔?所以我想了解您當時的心理斗爭?最后是如何做抉擇的?
丁曉兵:其實我一直想把這個榮譽的包袱卸掉,我打完仗了下來以后讀了一本居里夫人的自傳。她說她得了諾貝爾獎章以后,她還在給女兒做玩具,榮譽與未來無關。我讀了以后很震撼。
我從前線回來以后,當時安徽宣傳的規模非常大,我的感覺很好,有一點自我陶醉。我的父親是一位老兵。當時市領導帶領我一起去拜訪老紅軍、老八路。一進去以后我馬上就找到了另外一種感覺,打開他們的履歷哪一個不是九死一生,充滿傳奇?當他們把軍功章拿出來的時候,我就蒙掉了。忽然就感覺自己太膚淺了,在他們面前我有什么資格可以自我陶醉?
后來,有一個大學生給我寫了一封信說,在生死考驗面前,你稱得上英雄,假如10年20年以后,仍有事跡在你身上出現,我才能稱你為當之無愧的英雄。
榮譽也有雙重性,就像雙刃劍一樣,把握得好可能會成為我們前進的動力。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就可能成為背在我們肩上的包袱,甚至是懸在我們脖子上的利劍。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能不能正確的定位自己,認識自己,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特別是在那么多的榮譽面前,對于一個19歲的人,突然來了那么多的榮譽,弄不好就找不著北了。我一直嘗試著甩掉這個包袱,但是實際上沒有完全甩掉。
真正讓我醒悟過來的就是一名戰士得了抑郁癥,后來自殺了。當時我感覺非常痛苦。當時戰士們給我塞條子,他們說我們敬重你在戰場上是一條漢子,那么在名利面前我們希望你仍然是一條漢子。一個人如果自我意識過重,往往心地和眼界就非常狹窄。我們古語有一句話叫做“私欲重者有偏執”。所以經過了這件事后,我把用了好幾年的假肢拿掉了。以前出去老是在乎別人怎么看我。所以那一年我覺得不僅是我脫掉了假肢,更重要的是扔掉了心理上的包袱。
分享到: